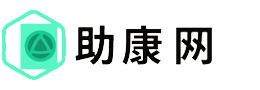五峰山大桥上的“东北三兄弟”
1月22日,腊月二十三,东北小年。长江上,寒风呼啸,凛冽刺骨。
晚上九点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淮安高铁基础设施段五峰山大桥车间宿舍内,吕文举挂断和母亲的视频通话,准备开始晚间作业任务。
今晚的作业点在车间1公里外的五峰山长江大桥上。22:00,对照“三确认”单,吕文举和同事们开始准备今晚“天窗”作业的工具材料。
1月23日00:05,驻站联络员发出指令:“调度命令已下达,可以上道。”吕文举和同事们乘坐电梯升到大桥南引桥桥面,往正桥走去。此刻,室外的温度已降至零下,越靠近江心风越大。
00:20,他们走到作业地,顺着十几米的爬梯下到墩台上。大桥支座就在防尘罩里。今晚4个小时的“天窗”时间内吕文举他们需要将6个墩台上的30个支座全部保养一遍。
临近春节,重点设备的检修频次都在增加,能够在节前多检查保养一遍设备,在吕文举他们看来很重要,因为这能让列车运行更顺畅、旅客体验更好。
将支座防尘罩四个面八扇玻璃逐个抵牢,打开四个口,吕文举从墩台面跨上支座,弯腰半蹲着垫步挪进防尘罩内,开始擦拭起支座镜面板。
刚开始时,擦拭的速度都很快。他们上跨弯腰偏头探身,不断在防尘罩的四个口来回穿梭,虽然罩内高度很低,空间狭小,但经验丰富的他们很快便能擦完一个。
等擦完十来个,他们的速度逐渐慢下来,酸麻感从四肢传来。为了让腿部不因长时间蹲着而酸胀,吕文举会仰着将腿伸出防尘罩外抖一抖,这是他的一个小诀窍。
支座保养的工作是枯燥的,特别是对于这些适应了快节奏生活的00后青年来说,一样的作业步骤重复几十遍,考验的不仅是体力还有精神。
桥隧工李俊良喜欢在作业时哼唱,且自带rap。入职第一天看到曾创造七项世界第一的五峰山大桥横越于长江之上时,这个辽宁人被震撼了,他知道今后的战场就在这里。
李俊良说,干铁路当桥隧工他曾经后悔过。从东北大老远跑到江苏来,干着卖力的活,熬着无数的夜。夏天酷暑难耐,冬天寒风刺骨。要是回东北老家开间小店,是不是会更快活?
但每次作业结束从桥上下来,站在宿舍窗前遥看,听着高铁从大桥上“哗”的一声疾驰而过,他又打消了“小店啤酒热炕头”的念想。“这辈子守着这咽喉要道,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
李晨是当晚作业组里年龄最小的,和吕文举、李俊良一样都是东北人。李俊良家住辽宁抚顺,吕文举是黑龙江鹤岗人,而李晨的家则在更北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
由于经常在一组作业又都是东北人,同事们都称他们为“东北三兄弟”。
同事们用猿臂蜂腰形容李晨。蹲在支座防尘罩口,他可以直接探身伸手擦拭最内侧的镜面板,纤细的胳膊好似不会累的机械臂,不停在镜面板上挥舞。
寒风呼啸,但李晨的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珠。他抬手用胳膊蹭了蹭,将领口的拉链向下拉了拉。
他记得第一次上桥时,周围一片漆黑,只能透过头灯光看到眼前十来米,耳边除了风声就是湍急的江水声。顺着爬梯下爬十几米到墩台上,头灯没法照到脚下,他根本不敢动。三年过去,他已经习惯把自己交给这漆黑的夜晚。
桥隧工会随身背一个工具包,里面装着工具和纸笔,用来处理和记录需要整治的事件。为减轻负重,他们一般不携带食物,只带一壶水。
长时间作业很消耗体力。02:30,三人席地而坐,闭目养神。安静下来,他们仿佛也像这座大桥一样,被黑夜吞没了。
“赶紧干吧,一会汗干了会感冒的。”十分钟后,吕文举忙着招呼大家继续作业。
03:30,天空依旧漆黑一片,所有支座保养已经完成。
顺着爬梯爬到桥面,江风依旧呼啸着。压紧安全帽,将棉衣拉链拉到顶,桥隧工们顺着来时的路返回。
晨曦中,大桥上的春运列车飞驰而过,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正在回家团圆的路上。忙碌了一宿的三名东北小伙,则刚在宿舍里躺下,稍事休整为下一次凌晨保养作业而准备。
声明: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